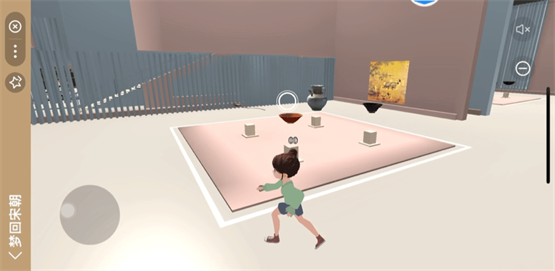快看:都是汉高祖刘邦沛县起兵的同乡,为什么卢绾可以获封异姓王?
在楚汉战争过程中,刘邦为了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,一方面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王,如张耳、英布、吴芮、臧荼等,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,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,如韩信、彭越等。不过刘邦沛县起兵的骨干却几乎都是封侯,如萧何、曹参、樊哙等,只有卢绾作为发小及同窗,被封了燕王,那么,为什么为何只有卢绾获封异姓王?
卢绾幼年交好刘邦,二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,作为发小及同窗,深得刘邦的信任,刘邦当泗水亭长时,身随左右,共同起兵,刘邦称帝后,卢绾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皇宫,与刘邦的弟弟刘交一样受到极度信任,传递各种隐秘的旨意。
因此,作为功臣中刘邦最为亲近之人,卢绾的受封标志着刘邦整体分封策略的转变。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自还定三秦开始,刘邦便有意识地着力重建郡县体制,然而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,不得不采取分封异姓诸侯王的策略。在击败项羽以后,刘邦仍试图恢复郡县,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汉朝无法有效控制原六国故土,而卢绾受封燕王则标志着刘邦放弃直接恢复郡县,而逐步转向分封同姓王,走郡国并行制的策略。
首先看一下刘邦在楚汉时期的扩张
在楚汉争霸的初期,刘邦先是还定三秦,后逐步向韩魏地区扩张,而在这一过程中,设置郡县一直是刘邦的主要规划:
二年,汉王东略地,塞王欣、翟王翳、河南王申阳皆降。韩王昌不听,使韩信击破之。於是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渭南、河上、中地郡;关外置河南郡。
汉王遣将军韩信击,大破之,虏豹。遂定魏地,置三郡,曰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。
然而,在楚汉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,刘邦项羽对峙于成皋、荥阳,韩信率军北上时,刘邦的郡县计划受到了挫败:
遣使报汉,因请立张耳为赵王,以镇抚其国。汉王许之,乃立张耳为赵王。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,韩信请立张耳为王的理由是“以镇抚其国”。
井陉之战发生于汉三年(公元前204年)十月,此战后汉军延续了此前设置郡县的方式,“置常山、代郡”,而“乃立张耳为赵王”则被记于汉四年(公元前203年)十一月。
这说明在井陉之战的胜利后,韩信沿用了汉军以往战略,在赵地设置郡县,然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仍难彻底控制,以至于被迫向刘邦请求“立张耳为赵王,以镇抚其国。”
类似的事更为明显的发生于韩信请立为假王时:
汉四年,遂皆降平齐。使人言汉王曰:“齐伪诈多变,反覆之国也,南边楚,不为假王以镇之,其势不定。原为假王便。”
汉王大怒,骂曰:“吾困於此,旦暮望若来佐我,乃欲自立为王!”
如“镇抚其国”类似,韩信在此提出的理由是“齐伪诈多变,反覆之国也”,这一方面是对齐地风俗的评价,另一方面也是对彼时政治形势的描述,直到垓下之战前夕,仍需“(曹)参留平齐未服者”,说明在楚汉战争进入尾声时,汉军仍未彻底征服齐地。
在赵、齐两个例子中,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:第一,赵、齐的封王经过与请求说明,在秦汉之际的背景下,以郡县制控制山东六国的确存在困难,尤其是赵、燕、齐、楚地区;第二,在封王过程中,刘邦的态度是极为激烈的。
井陉之战结束于汉三年十月,然而直到汉四年十一月张耳才正式封王,这说明刘邦对此是并不情愿的,他仍然希望尝试以郡县统治赵地。而当韩信的请求发来,刘邦更是直接破口大骂,这充分说明了刘邦对于直接采取郡县制仍然保持了极深的执念。
刘邦最终接受分封异姓诸侯或许在垓下决战前夕:
谓张子房曰:“诸侯不从约,为之奈何?”对曰: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,今可立致也。”
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:“并力击楚。楚破,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,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。”
因此,垓下之战前所确认的并非后世常见的君臣关系,而是盟主与诸侯之间的关系,而这种关系则在韩信领衔异姓王的劝进上疏中表现的最为明显:
先时,秦为亡道,天下诛之。大王先得秦王,定关中,于天下功最多。存亡定危,救败继绝,以安万民,功盛德厚。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,使得立社稷。地分已定,而位号比拟,亡上下之分,大王功德之著,于后世不宣。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。
大王起于细微,灭乱秦,威动海内。又以辟陋之地,自汉中行威德,诛不义,立有功,平定海内,功臣皆受地食邑,非私之地。大王德施四海,诸侯王不足以道之,居帝位甚实宜,愿大王以幸天下。
在此,韩信等异姓王均强调了刘邦的分封之德,这同样也是对于刘邦的一种提示。以汉王即帝位为标志,汉初的政治格局得到第一次确认,与其说是汉初的形势是秦始皇式的“并天下”,不如说是“共天下”,而刘邦此前试图全面恢复郡县的尝试被迫搁浅。
然而异姓王格局并不是汉初政治的终点,以楚汉战争的结束为新的节点,刘邦开始了新一轮对异姓王的“再征服”。
在传统观点中,垓下之战后的汉军的胜利已经得到了确认,平定异姓王仅仅是汉朝内部的反覆,然而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并非如此,平定异姓王的危险与楚汉争霸并无本质区别:
萧丞相营作未央宫,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。高祖还,见宫阙壮甚,怒,谓萧何曰:“天下匈匈苦战数岁,成败未可知,是何治宫室过度也?”萧何曰:“天下方未定,故可因遂就宫室。且夫天子四海为家,非壮丽无以重威,且无令後世有以加也。”高祖乃说。
此时为汉八年(公元前199年),无论是刘邦还是萧何,均认可“天下方未定”“成败未可知”,与之类似,此前贯高在谋刺高祖时也曾表示:“夫天下豪桀并起,能者先立。”而在劝谏刘邦定都关中时,娄敬、张良同样将东方诸侯视为假想敌:
陛下入关而都之,山东虽乱,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。
夫关中左殽函,右陇蜀,沃野千里,南有巴蜀之饶,北有胡苑之利,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
因此平定异姓王的过程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容易,汉朝时刻处于倾覆的危险之中。
基于这种背景认知,再来看一看刘邦平定异姓王的过程:
在“齐王韩信习楚风俗,徙为楚王”之后,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齐地并非分封,而是置为郡县。随后,“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”,在平定之后其地也被置为南阳郡。这说明在平定异姓王初期,刘邦再次着手恢复郡县制。
然而以燕王臧荼反,刘邦立卢绾为燕王开始,刘邦对于异姓王的征服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他开始放弃全面恢复郡县的尝试,转向了分封同姓王的新政治格局,而分封最为亲近的卢绾,则是对于这一转变的“试探”。
欲王卢绾,为群臣觖望。及虏臧荼,乃下诏诸将相列侯,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。群臣知上欲王卢绾,皆言曰:“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,功最多,可王燕。”诏许之。
关于群臣之间功多的问题其实在当年之初早有有过讨论,当时功臣以曹参功最多,最终在刘邦的亲自拍板下确定萧何功最多,无论如何都不涉及卢绾,此时群臣以“卢绾功最多”为由请立燕王显然并非真意。
他们请立卢绾的实际理由是卢绾与刘邦亲近,“知上欲王卢绾”,但是在正式的谏言中仍需抬出作为秦末共识的“功多”之论。
卢绾受封意味着刘邦试探的成功,同时也暗示了汉初政治形势的悄然变化:皇权正在逐步确立,但改变被隐藏在过去的话语之中。
无独有偶,在废韩信楚王时,刘邦同样“遂会诸侯于陈,尽定楚地”,尽管无法了解“会诸侯于陈”的具体经过,但是显然,在刘邦实现废楚王的过程中,仍需在仪式上保持“共天下”的形式。
就在废韩信十余日后,刘邦正式下诏开始了分封同姓王的进程:
齐,古之建国也,今为郡县,其复以为诸侯。将军刘贾数有大功,及择宽惠修絜者,王齐、荆地。
与荆王刘贾一并受封的还有楚王刘交、齐王刘肥,在彻底平定异姓王后,又立兄仲、子恒为代王,子如意为赵王,子恢为梁王,子友为淮阳王,子长为淮南王,兄子濞为吴王,子建为燕王,最终形成了同姓王格局。
如果将汉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的同姓王格局与汉五年的异姓王格局进行对比,会发现,在平定异姓王之后,由汉直接郡县管辖的土地反而变少了:朝廷不仅吐出了齐地,而另行分封了代国。结合刘邦此前两次恢复郡县的尝试,这是否意味着汉朝集权化的退却呢?
其实在分封卢绾前后,汉五年(公元前202年)、汉七年(公元前200年)分别发生了两件事,而这两件事暗示了汉初皇权的走向。
汉五年,高祖置酒洛阳,向功臣们询问自己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的原因:
高起、王陵对曰:“陛下使人攻城略地,所降下者因以予之,与天下同利也。项羽妒贤嫉能,有功者害之,贤者疑之,战胜而不予人功,得地而不予人利,此所以失天下也。”
高祖曰:“公知其一,未知其二。……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
这段对话耳熟能详,经常被作为理解项羽失败的原因,不过高起、王陵所回答的,其实是楚汉争霸时期的“标准答案”。
刘邦的胜利与其在楚汉战争期间的分封策略高度相关,甚至其最终得以称帝,也是因为诸侯感念其分封之德,而这一共识更是贯穿了整个楚汉战争时期。
早在汉中对时期,韩信便指责项羽妇人之仁:“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,印刓敝,忍不能予,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”其言辞与高起、王陵并无一致,并进而规劝刘邦:“以天下城邑封功臣,何所不服!”其观点与称帝上疏一致。
无独有偶,曾在垓下之战前劝谏刘邦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,今可立致也”的张良,此前在反驳郦食其时也曾强调:“天下游士离其亲戚,弃坟墓,去故旧,从陛下游者,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”
换句话说,无论是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,还是确立政治秩序的称帝上疏中,分封的重要性都是汉初的基本共识,然而在汉五年的这次置酒对谈中,当高起、王陵重新摆出此前的“标准答案”时,刘邦不认账了。
此三者,皆人杰也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
在这种表述中,刘邦改变了了自己与功臣的关系。在劝进上疏中,刘邦与异姓王实为盟主与诸侯的关系;而当刘邦在谈及“吾能用之”时,实际上悄然将二者的关系转变为后世的君臣关系。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韩信,彼时裂土一方的异姓诸侯,在此种表述中被转变为与萧何近似的汉家臣子。
如果说对于汉五年刘邦与功臣对话还有不同解读方式的话,那么汉七年叔孙通起朝仪则更为明显的展示了政治文化的转变:
汉五年,已并天下,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,……群臣饮酒争功,醉或妄呼,拔剑击柱,高帝患之。
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。……汉七年,长乐宫成,诸侯群臣皆朝十月。……竟朝置酒,无敢讙譁失礼者。於是高帝曰: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
当异姓王上疏请刘邦称帝时,刘邦认为所谓帝号不过虚名,“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,虚言亡实之名,非所取也。”然而在叔孙通起朝仪后,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
从君臣置酒对谈到封卢绾为燕王,从会诸侯废韩信到叔孙通起朝仪,汉初的皇权政治文化便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确立的。
在诛吕之乱中,齐王刘襄在书信中提及:“悼惠王薨,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。”这或许说明,同姓王的继位不仅仅是父子相承,还需得到汉帝的认可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,汉初异姓王张敖继承张耳王位时,仅仅表述为“子敖嗣立为赵王”,其中“嗣立”所暗示的政治程序显然与刘襄有所差异。
刘邦如何认识自己所留下的遗产不得而知,然而就其在汉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留下的诏书来看,他似乎彻底放下了曾经对于郡县帝国的执着:
吾立为天子,帝有天下,十二年于今矣。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,同安辑之。……吾于天下贤士功臣,可谓亡负矣。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,与天下共伐诛之。
在几乎是要盖棺定论的时刻,或许是政治形势的限制,或许是自己内心的解脱,刘邦回归了“共定天下”的政治表述,也认可了同姓王的政治格局。
刘邦平定异姓王、分封同姓王是汉代重新走向大一统的重要一环,“郡国并行制”是当时刘邦能够选择的最优出路,虽然它从来不是刘邦最想走的道路。